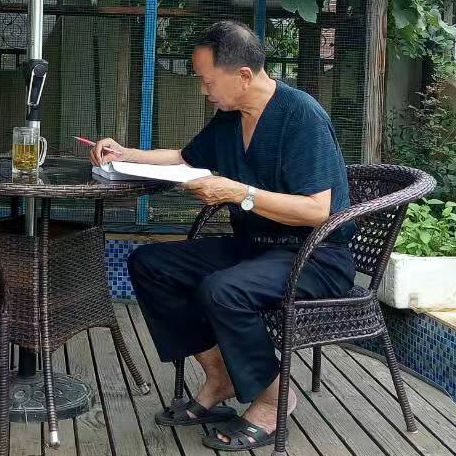南唐村吴氏文化考察
《我与吴文化》民俗文化之一
南唐村吴氏文化考察
永新,是一个有着悠久和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古县。尤其在南乡南唐村,各种具有传统吴文化色彩的民俗活动,至民国时已达到鼎盛时期。现撷其三项,以飨读者。
一、 庄 堂
庄堂,习武之场所也。在冷兵器时代,乡人要武装自卫,必须通过庄堂的训练和演习,才能掌握一整套攻防本领。
旧时,民间因山林土地权属、水源分配、宗族矛盾、风水迷信、民事纠纷等引起的武装械斗,时有发生。由于法制缺失,官府无为,那种矛盾通常只有诉诸武力才能得到解决。既然武装械斗的发生不可避免,习武之处——庄堂,便在永新乡间应运而生,且经久不衰。
南唐村,严格地说她是一个宗族名,清一色的吴姓,约八百余户,是当地一大望族,下分九个自然村,三个村委。之所以名之“南唐”,是为了纪念永新吴氏始祖吴皙于五代十国之南唐时期(约公元950年),由九江赴永新任县衙主簿,并肇基永新而命名的。
南唐地处万年山水系最末端,自然灌溉十分困难,每逢大旱季节,与上游十三社(今烟阁乡大部)争水之纠纷,时有发生,械斗也在所难免。为了生存,南唐人自古就有起庄堂习武的传统。“不进庄堂,算不得男子汉”这一古训,在南唐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。为了生存,千百年来,习武已经成为南唐成年男子的必修课。
庄堂,多半以自然村为单位举办。南唐人开庄堂,一般不用向外聘请师傅。因为,长年开办庄堂,其中有不少优秀者,自然都成了师父。不光如此,还有师父“输出”,不少佼佼者,还被外地请去做师父。师父坐在庄堂里的时间并不多,只是隔三差五地前去指导一番。师父的待遇并不丰厚,一年下来,也就是七八块大洋。可就是这几块大洋也不是好拿的:年底送师父回家过年时,徒弟们必然会想方设法地使招“留”师父,实际上是要和师父较量,如果师父在徒儿们面前失了彩,那他这一年的辛苦就算泡汤了。所以,聪明的师父们,是不会轻易将全身本领传授给徒儿们的。所谓“十步留一步,别让徒弟打师父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
庄堂设在祠堂内,每年的正月十六日起(开)庄,长年开办,只是农忙时,才停办数日。一般是利用晚间休息时间,到秋后,为了赶明年正月“出灯”(表演),才日夜操练。在庄堂习武是没有报酬的,全是自愿参加。但如果外出表演有收入,则能按一定比例得到一点分成。表演一场的收入也很可怜,仅1吊零200钱,按时价,1吊钱仅能买到了3斤左右的猪肉。折如今人民币60余元,按照16个人分,每人仅人民币4元不到。
起庄时,必先安好“师头”,“师头”是武林祖师爷神位的意思。神位制作很简单,先在祠堂正厅右边柱子上铺好金银纸各一张,然后将三颗竹钉钉在纸上,再用一块红布蒙住竹钉即成。
庄堂也是犯事的温床,参加庄堂习武者大多是年轻人,熬到半夜,大多数人已饥肠辘辘。此时,外出偷点鱼呀鸡狗和果蔬来充饥的事,也时有发生。
在南唐庄堂里练习的主要是拳术和棍术,另有三节龙灯、舞狮和盾牌舞等。
南唐的拳是一种独特的中矮庄的庄式拳套路,习惯称其为“梅花六九”。与别村的拳术套路不同,它主要是原地“打四门”的拳术套路,共八式,各式变化无穷。这种拳看似简单,其实它的实用性很强,是一种以防御为主,进攻为辅的传统武术。这也充分体现了南唐人习武的自卫性质。所以,它从不向外村人传授,只是在本村内部相互教练,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。
南唐棍与矛的套路也是独式的,号称“吴式棍”,其选材是用一种名为“对节”的刚韧木材,长一丈余,头粗尾细,可作棍和矛两用。安了矛头时是枪(矛),去掉矛头又可作棍用。作棍用时,双手始终握着棍头,像用枪和梭标一样。因此,南唐的棍式也可以说是枪式,或者说是棍枪结合的一种特殊招式。说是棍式,它可以用来点打横扫;说是枪式,可以左拨右挠,还可以用棍尾冲刺。棍式和枪式可交换使用,灵活机动,实战性强。
南唐庄堂棍式套路一是“野鸡闯河”,二是“打四门”。“野鸡闯河”是枪式,分六式,即启势、开手、出击、散打、取胜、收庄。“打四门”是棍式,分八式,即:开势、打南门、打西门、打北门、打东门、倒棍、左右扫棍、收势。
俗话说得好,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。进庄堂习武,没有个三年五载是不可能出师的。进庄堂习武的人,除了必须有坚强意志,还须有灵活的头脑。
庄堂习武有两大功能:一曰自卫性械斗,一曰表演。
1、自卫性械斗:
械斗,永新乡间称之为“打大阵”,是宗族或村之间因某些矛盾而引发的武装械斗。
南唐人的武术十分厉害,素有“棍尾上长谷”之谓,意为全靠武力才能保证有水种田,才能有好收成。水,是农业的生命之源,也是南唐人开庄堂习武之主要目的。
每年的七八月份,是农田灌溉的关键时节。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,也正是南唐灌区最缺水的季节。为争水源,与上游十三社的械斗时有发生。而一旦械斗发生了,“十八岁上江口(分水口)”,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,谁也不能抗拒,否则,将有被“隔族”(开除族籍)的危险。
是时,南唐各村分别杀猪磨豆腐,集体起伙,全村动员,一副大战前夕的备战态势。出发前,在祠堂里誓师,应征者全副武装:男人头戴用竹子编制的“毫须”(类似藤帽),手持棍棒、大刀。女人腰系装着石块的竹鱼篓,紧随自己的男人身后。如一旦丈夫与人交战,妻子则在旁以石块助战。那种夫妻上阵的壮举,是古今中外任何战争场合所少见的。
誓师大会由族长主持,宣布纪律、队形序列、主攻手名单、与南唐其他村的会合时间、地点及善后事宜。对于在械斗中死伤的亲属,族里统一用祠会公款或按户摊款安葬死者、抚养遗孤和治疗伤者。这种举措,从制度上解决了参战者的后顾之忧。
善后事情很多,如“议凶手”。“议凶手”,是旧时械斗的一大特色:目的是万一如果打出了人命,需要有人马上出来做“替死鬼”。这个人选,多半是无家无室,生活无靠却又有父母需要赡养之人。确定人选后,当面议好价钱和确定抚恤方案,并立下生死文书,一旦出死,此人便慷慨赴义。此去九死一生,多于水牢和“随桶”(一种周边插满刀子的木桶状刑具)中痛苦地死去,鲜有善终者。
这一切做完后,杀雄鸡歃血为誓,众人喝血酒毕,族长一声令下,众皆应声如雷,慷慨出征。走在前面的是庄堂师傅, 战场在觉滩江分水口——三江口。
械斗一般发生在日出以后,因为那个时候正是南唐人从分水口撤岗的时候。十三社的人选中这个时候在半路上搞突然袭击。实战时,一般三人为一小组,武师或主攻手在前,两旁各一名护卫,形成一个犄角状,互为照应。武师这时是阵中的主心骨,也是衡量武师本领的时候。这种械斗没有阵法,也没有多大的谋略,其实是一种遭遇战,双方见面便打,直到打得昏天黑地,直到一方有人负伤倒地。此时,如果旁边的看客偏向胜方,齐声吆喝“某方倒人啦!”士气便大受影响,战局便会一边倒。战斗的胜负,往往就操纵在这些看客的手里。所以,上阵的人最恨的不是对方的敌手,而是那些看客。
南唐人面对的是强手,是由十三个社(相当于今天十三个村委)组成的“联合舰队”,兵力悬殊,且又在对方地面上作战。但十三社人多不同心,可谓乌合之众,根本没有南唐人的战斗力。更有趣的是,十三社里面也有不少是吴姓,这使他们处于两难的地步:对方是同宗,怎能兵刃相见?而自己地处十三社,受益于同一水源,又不能不出阵,要不,怎么有水灌溉?因此,他们与南唐人私下约定:大凡十三社的吴姓,都分别做上记号,以防误伤。这样一来,十三社的力量更弱了。就这样,在每次械斗中,南唐人依仗自己在庄堂中练就的过硬本领,从来没有真正被打败过。
械斗中死伤血案,常有发生。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:双方杀死的是男人,如官府不追究,各自安葬。但无论如何不能杀死看客和女人,否则,禀官后官府将会以杀人罪逮人。杀人者偿命,天经地义,但最后的结局,多以另请替死鬼作凶手结案。替死鬼的结局是很惨的,打入死牢后,往往是活活地被折磨而死。
械斗中杀死女人的事件,也曾发生过:民国二年,南唐前房村与黄淇村龙姓发生了械斗。其时龙姓势众,大有摧城之势。危难之机,南唐东边村十八个“扁担客”恰好路过,见同宗势危,马上抽出扁担助战。那十八条扁担,像十八条蛟龙,没几下工夫便将龙姓打得落花流水。在龙姓村头,龙姓一女人仗着有男人不伤女人的规矩,对吴姓破口大骂,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出了口。这时,东边村一年轻小伙子受不了那股气,从旁人手中接过一杠枪,从高岸飞身而下,用枪尖直刺那女人的下体,活活将她捅死。事后,龙姓告官,吴姓花高价请出一个“凶手”,才了结此案。
“南唐人个个有两下”, “打得南唐,难打东边”,这些与习武有关的口头禅至今仍在永新老辈子人中广为流传。和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存法则一样,南唐人为了生存——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方式,世世代代被迫开庄堂习武,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和生存权利。
南唐人与外村人最后的一次械斗,发生在1974年10月。其时,南唐前房村与相距十里之远的柞源史姓发生山林权属纠纷。那天,早已埋伏好了的柞源人,趁前往现场干活的南唐人不备,向手无寸铁的南唐人发起突然袭击。此案造成了一场一死二十余人受轻重伤的械斗惨剧。事后,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法律的偏见,受害方也有人被判以重刑。
数百年来,像这样的械斗,不知发生过多少次,不知造成了多少个家庭悲剧?每次械斗的最后,无论表面的胜负如何,其实都是输家。
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健全,械斗,那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陋习,正在远离人们的生活。随之,像“起(开)庄堂”那种在民间流传了数百年的习武传统,也正在淡出人们的记忆。如今,当年在庄堂中担当过角色的后生们,也都垂垂老矣。就连能在现场演示几下的人,也已廖若寒星,去日无多了。
2、表演
表演,是庄堂的另一大功能。
正月半(元宵前),是农村各种技艺表演的黄金时间。届时,各种戏剧,如三角班、采茶剧、汉剧和龙灯、狮灯、盾牌舞,竞相出台表演,成为农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辛辛苦苦练习了一年的庄堂的哥们儿,此时正是亮相的极好时机。从初一开始,他们便出门“打灯”(表演)了。先是“打”家门(宗族),其后便“打”友好乡邻。
“打灯”,是有一套既定的“灯路”、程序和礼仪的。
“灯路”是先至亲同宗,然后再按亲疏依次排列,最后是异姓乡邻,绝不能乱了“灯路”,否则,将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程序是:前一日,先由一人持灯笼前去下帖子。翌日,由士绅、老成、师父三人各持一盏灯笼前面开路,两个挑盾牌、一个挑花烛鞭炮的随后。在他们后面的是十六个庄堂哥们儿白汗巾裹头,身着紧身服,手持棍棒等武器紧随其后,浩浩荡荡向目的地开拔。
礼仪是:每到一村头,东道主必有士绅、老成等按梯队三步一作揖恭迎。但再客气,也不能接过人家的灯笼。否则,有砸人家招牌之嫌。
按规矩,开台拳是由年轻汉子表演。如本地也起了庄堂,得先拜钉在右柱子上的“师头”,再拜祠主和四方神灵,然后向台下一个深揖,向台下的同行和前辈致礼,请多多包涵。而最后谢幕的包台拳,却是由庄堂里武艺最高的人露手。
先表演三节龙灯,然后是狮灯,即狮子跳台,跳台是一项与现代体操跳木马有点相像的一种运动。台,一般是用祠堂内的神台,比一般方桌要高出许多,没有几下真工夫,要想在台上台下表演那么多高难度的动作,是不可理喻的。其后是拳棍交替进行,拳无踪,棍无影,精彩的表演,不时赢来台下一阵阵的喝彩。
拳棍表演结束后,便是“喝牌”(表演盾牌舞)。届时,打击声和嘶喊声,将这场武术表演推向了高潮。随着盾牌舞的嘎然落幕,观众的心还沉浸于惊心动魄的古战场之中。
庄堂,作为一种冷兵器时代的民间武术团体,早已由辉煌走向没落。
解放初期,庄堂时开时停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随着政治的原因和水利设施的完善,人们不用再去为争水而动武了。随之,庄堂已销声匿迹。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,庄堂曾经一度又在南唐各村兴起。但是,好景不长,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,不甘寂寞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涌向外面的花花世界,庄堂又一次,也许是永远地沉寂了下来。如今,在南唐村能表演拳棍、滚狮和盾牌舞的,只剩下几位垂垂老者矣。
庄堂,也许会永远地告别南唐村。但武术,作为一种能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,会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钟爱。
一个时代结束了,但愿它的精神能永远地传承下去。
二、千古一绝——盾牌舞
如果说庄堂里习武是为了自卫,那么南唐吴氏演习的盾牌舞,则纯粹是为了表演,
盾牌舞,是南唐村祖传下来的一项集武术与艺术于一体、风格独特的作战操式的舞蹈。2006年,被文化部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。
盾牌舞,原名“藤牌舞”,以其盾牌原为葛藤编织而名之,又因其表演过程中常有惊天动地的吆喝声,故乡间又称之为“喝牌”。但盾牌舞起源于何时?目前尚无定论。有史前说的,说是起源于早期人类的原始舞蹈,也有起源于汉朝的藤牌操之说;较“权威”的说法是起源于太平天国之说:说是太平天国失败后,散落在南唐的将士感其恩而传授的,众说纷纭,已无可稽考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那就是盾牌舞只属于南唐,别无“分店”。
盾牌舞有一种屈原笔下《国殇》里的悲壮场面和“身既死兮神以灵,魂魄毅兮为鬼雄”的英雄气慨。如果说它与别的舞蹈有什么不同的话,那就是它的大气,那种能力拒万敌于方阵之外的磅礴大气。
其实,盾牌舞并不十分复杂,全场表演时间也不过十几分钟;人员也不算太多,只有十个人。表演武士分为两军,每军武将一人,士兵四人。武士头廛长白汗巾,上穿黑色镶白边胸花对襟短衫,下着黑色紧口裤,脚蹬黄麻草鞋,领队武将头缠黑汗巾,手持带环长柄钢叉,其余武士则一手持盾牌,一手紧握响环短刀。操练形式、阵势颇具冷兵器时代战斗场面。其时,幕后锣鼓、唢呐齐鸣,为武士表演配合节拍,鼓舞斗志,使表演更为壮观。
盾牌舞主要有八个阵式:开演仪式、四角阵、长蛇阵、八字阵、黄蜂阵、龙门阵、荷包阵和打花牌等。
开演仪式古朴而肃穆,在悲怆的唢呐声中,取一雄鸡歃血酒而拜四方天地。然后,惊天动地的一声呐喊,武士分站四角,武将叉手左冲右突,一下子就把人带到“操吴戈兮被犀甲,车错觳兮短兵接”的古战场。接着阵形一变,成为有头有尾的长蛇阵。武士们飞步鱼跃而上,显示出非凡的武功。强攻时刀叉相接,铁环鸣响,旌旗蔽日。软攻时,缠绵悱恻,风情万种。猛然,锣鼓骤起,突变为八字阵,两军对垒,双方森严壁垒,杀气腾腾,大有吞并日月之势。
“旌蔽日兮敌若云,矢交坠兮士争先”,随着急促的鼓点,霎时,响环齐鸣,武士齐声呐喊,惊天动地,分外壮烈。在一段走台的间隙后,八位武士并排滚动,尤如黄蜂出洞,铺天盖地席卷而来,势不可挡。这便是黄蜂阵。紧接着是包围与反包围的龙门阵、荷包阵。最紧张激烈的“打花牌”,使整个表演形成高潮。武士们怀着“首身离兮心不惩”的英雄气慨,拼死冲杀,短兵相接,表演武士亮出平生武功,拼尽全力,真刀真枪地打出了令人眼花缭乱而又心惊胆颤“跳牌”、“嚎牌”、“腰牌”、“滚牌”、“躲牌”、“花牌”等。
“凌余阵兮躐余行,左骖殪兮右刃伤”。你看:锋利如霜的短刀上下飞舞,刀刀刺向叉手。叉手则凭借沉稳坚实的“丁桩步”和“矮桩步”一一化解。寒光闪闪的钢叉手又刺又砸,钢叉刺破蒙上了牛皮的竹制盾牌。有时叉手奋力一击,竟将盾牌劈为两半。面对这凌厉的攻势,刀叉相击,火花四溅,凭借坚实的武功,武士们疾而不乱。这一系列举动,表现出高超的搏击技巧,令看客心惊肉跳,叹为观止。
“援玉枹兮击鸣鼓”与其它舞蹈不同,盾牌舞的音乐也别具一格。在打击乐的基础上,又吸取了采茶戏高亢的唢呐曲牌,随着剧情的发展,有时勇武雄浑,如万马奔腾;有时又如哭如泣,似秋水低咽;有时又丽日和风,人在原野上信马由缰……
盾牌舞一路走来,既有过辉煌,也有过灾难和低迷。但它最受人们的喜爱,是南唐人出灯时最后的一个压台节目,也是最精彩,最受人欢迎的一个节目。那时,各地的狮灯不少,可是能表演盾牌舞的却只有南唐吴姓数家,故南唐的狮灯特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。
1953年,南唐村的盾牌舞,曾代表中南地区的优秀节目,选拔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民间艺术会演赛。在中南海怀仁堂表演时,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前排就坐观看,并受到他们的亲切接见和鼓励。文革中,盾牌舞也在劫难逃,从此沉寂了十多年。直至1976年冬,上海科技电视台才将盾牌舞拍成电视片,介绍到台海彼岸。1985年江西电视台摄制组专程来到南唐,将盾牌舞拍成电视片,在省电视台播放。
2006年,南唐盾牌舞被国务院、文化部批准为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”。盾牌舞表演者之一吴三桂也被评为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”。其实,当年盾牌舞队健在的还大有人在,如:吴金仁、吴太口、吴细华、吴建华、吴玉龙、吴花仔、吴忠良、吴凤香、吴大江、吴厚发等十余人。至于为何只有一人荣获“非遗传人”的殊誉?个中原委,不得而知。
南唐盾牌舞,如今也面临青黄不接和濒临失传的困境:老的一个一个地去世了,在世的表演者年龄最大的吴文降有八十多岁,最年轻的吴细华三十三岁。受市场经济的影响,没有资金的投入,很难再重组盾牌舞队,也很难再举行一场正规的盾牌舞表演。
正宗的南唐盾牌舞,前些年已被县文工团移植并加以改编,孰是孰非?不敢妄加评议。用“非遗传人”吴三桂的话说,祖宗传下来的盾牌舞被“卖”掉了。县文工团盾牌舞队已经取代了南唐盾牌舞队,连“非遗传人”也很难被邀外出参加表演。吴三桂的无奈,也道出了“非遗”的遗憾和尴尬。
三、等”五涧水”老爷
南唐村,在南乡是一个吴姓大族,宗族观念非常浓厚,对祖宗的崇拜,也相当虔诚。每年的大年初一至元宵节,都会将自己的祖宗像“请”到祠堂接受人们的礼拜。冬至日,也会在祠堂内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,其规模之大,毫不逊色于乡里的其它宗族。
可是,就是这样一个宗族观念极其强烈的地方,却每年都会举行一场最为隆重的迎送异姓先人的祭祀活动。而且一年到头都有村民轮流为他上香进供。对这一异姓先人的礼遇“规格”,显然超越了南唐人对自己祖宗的尊崇。
这场活动的名称,人们习惯地称之为“等五涧水老爷”。
“等”,在永新方言中意为迎接。“五涧水”,是南唐吴氏老居、新居、前房、上边、垅中等五村(其它几村因不受此水之益,故不在此列)农田灌溉中按时段划分的五份水。“老爷”,指的是清康熙年间的永新知县——姓黎名士弘。这里将“老爷”和“五涧水”联系起来,就是因为这位县老爷为南唐的农田灌溉出了大力,有大恩于南唐。所以,人们才会这样地感恩,黎知县才会在他死后数百年来,一直享受如此高规格的礼遇。
话,还得从300多年前南唐人的生存状态说起:
南唐地处万年山水系沉滩江的左边,因地势较高且距分水口较远,故稍遇天旱便无水灌溉。为了争水,南唐人与沉滩江下游十三社(相当于如今烟阁乡全部)的纷争和械斗时有发生,几乎每年都有死伤的命案报到官府,历代官府对此深感烦恼和无奈。
清康熙初年,福建长汀人黎士弘就任永新知县。不久,他就接到南唐与十三社发生械斗的报案。黎士弘不像前任一样关门办案,而是走出去,走到案发地现场办案。他来到沉滩江口,仔细地察看了灌溉系统的分布情况。发现流经南唐的水由于地势高,流速慢;又由于路途远,沿途水量流失大。如果按同等水量分配,南唐村真正得到的水量不足十三社的三分之一。所以,回到县衙后,黎士弘就沉滩江分水口案作出了公正的判决:“日出三江平流,日落吴姓独管”,从法律上正式确定了南唐吴姓在沉滩江灌溉区域内的合法地位。
水,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,也是南唐人能否在这方土地上生存下去的基本要素。黎知县的判决,使南唐人如拨云见日,获得了生存的权利。南唐人知恩图报,在黎知县还未离任时,就为他建了生祠。黎离任后,又为他刻了“去思碑”, 以载其德;雕了塑像,以祭其身。
从此,南唐五村人们形成了一个数百年(除文革外)不变的礼制——轮值祭祀黎老爷(习惯上称之为“五涧水老爷” )。早年的轮值接交日定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一,近年鉴于人口大都外出务工,村内空虚,故改为农历十二月十五日。
届时,新轮值方的男丁即使身在千里,也自觉地提前回归,参与“等五涧水老爷”活动。这是铁一样的规矩,没有任何人愿意打破。
交接前日(十四日)下午,上年轮值村的人们敲锣打鼓,将那尊供奉了数百年的黎士弘木雕像从神房中“请”到祠堂神台上“端坐”,并请来戏班,唱上两场大戏,为“老爷”送行。戏散场后,留下十数个壮汉守夜,陪伴“老爷”喝酒打牌,直至天明。
是日,一大早,人们就纷纷来到祠堂上香作揖,向“五涧水老爷”辞行。上午八时左右,下年轮值方的人们抬着彩轿,披红挂彩,敲锣打鼓地前来“等五涧水老爷”。在祠堂,人们恭恭敬敬地将头戴峨冠,身着多重绣袍,由于长年的香火熏陶,脸色变成“黑包公”一样的“老爷”和侍卫们抱上装饰一新的官轿。随之,铳爆齐鸣,先由两个扛着“肃静”和“回避”大牌的“差役”,敲着大官锣在前面开道。然后,四位“轿夫”在众人的一片吆喝声中,缓缓抬起官轿向大门走去。这时,各家各户带来的鞭炮齐鸣,“老爷”在人们一片祈祷声中,离开了他在此“居住”了365天的村子,又向新的轮值村走去。
“老爷”的官路是特殊安排的,要绕道而行,俗称为“游垅”,计有十余里之遥。浩浩荡荡的接送队伍少说也有一里之长。队伍所过之地,沿途百姓无不在自家门前燃爆和合掌祈祷,以示敬仰。每年此时,县里都有不少猎奇者前来观摩,来者无不被此场面所感染,无不为黎老爷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,获得老百姓如此爱戴而感到震憾。
约一个多时辰之后,迎送“五涧水老爷”的队伍来到新轮值主的祠堂门前,人们早就将一头大肥猪架上了屠宰台,一见“老爷”已到,屠手立马将猪杀了。这叫“杀拦门猪”,是永新南乡待客的最高礼仪,轻易不可为之。在一片惊天动地的鞭炮声中,“黎老爷”被抬进了祠堂正中央,并被抱出了大轿,安坐在神台之上。届时,全村老少无不前来焚香礼拜,连刚呀呀学语的儿童也跟在大人身后学着作揖打恭,其认真模样,既使人忍俊不禁,又令人肃然起敬。
一般年景,都要请来戏班或电影,唱(放)上三天三夜,为“老爷”接风洗尘。是时,八个大汉护卫在“老爷”身旁,陪伴“老爷”看戏,陪“老爷”过夜,直至天明。最后,“老爷”将被安放在一间宽畅明亮的神房内,全村按户轮值上供上香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一日三餐,从不间断。
数百年来,南唐人就是这样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地供奉着这位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,却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的前父母官。他们视“黎老爷”为生命,为保护“老爷”,有过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:文革中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,公社的造反派不让供奉一切神祗和祖宗,并四处搜寻“黎老爷”,必欲焚之而后快。南唐一老妪为防不测,将“黎老爷”用布包妥,当作襁褓背在自己的背上去田间劳作,日日如此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正是有南唐人的精心保护,“黎老爷”才躲过一场又一场浩劫,完好无损地保留至今。
据清同治《永新县志》记载:黎士弘,字媿曾,福建长汀县濯田乡陈屋村人。自幼聪明过人,好学博闻,进士出身,清康熙间由饶州(今上饶)玉山县县令改任永新县令。在永新三年,息虎患,修水利,兴学校,劝农耕,减赋税,剿匪寇,平冤狱,政声卓异,是永新历史上少见的几个好官、清官之一。
2005年10月,笔者为研究黎士弘,曾亲临长汀县博物馆和陈屋黎士弘故居,所见所闻莫不皆然。如今黎士弘故居破败不堪,黎氏后人仅存8户,人丁欠旺。时过境迁,睹物思人,不禁令人感慨不已。
◆声明:本站属非营利性纯民间公益网站,旨在对我国传统文化去其糟粕,取其精华,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做一点贡献。所发表的作品均来自网友个人原创作品或转贴自报刊、杂志、互联网等。如果涉及到您的资料不想在此免费发布,请来信告知,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予以删除。 全部资料都为原作者版权所有,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能下载作为商业等所用。——特此声明!
相关内容
- 2025-12-24 武穴吴氏文化《本修诗、词、文》五
- 2025-12-23 侗韵迎佳节 同心筑家园
- 2025-12-20 祠堂文化:中华家族传承的精神圣殿
- 2025-12-19 念师恩·悼文
- 2025-12-23 祠堂文化溯源(二)
- 2025-12-21 祠堂文化溯源(一):礼制传承中的祭祀圣地
点击排行
- 104-08县城里的小孩,人们,与游戏
- 203-17越绝书一
- 303-17越绝书二
- 401-30吴三桂诗词文艺汇编 (一)
- 501-15吴称谋诗词—— 参禅悟道...
随机文档
- 110-16修家谱时怎么写倡议书
- 209-19东汉永兴二年三月糜豹序存疑
- 303-18原籍广东广州府南海县水西...
- 411-27安徽肥东县高塘镇吴小郢宗...
- 511-04武进吴氏先贤吴竹似:24载...
 当前位置:
当前位置: